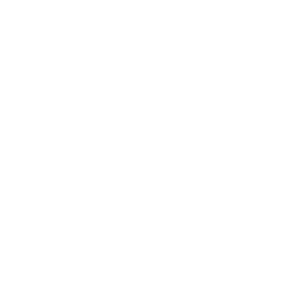对话张永和:建筑不是“广告画

4月8日,因为疫情推迟数月的首届“三联人文城市奖”颁奖典礼,终于如约来到成都。
此次活动以“重建联结”为主题,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,推动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的讨论。借此机会,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(下称“NBD”)对本次评选终审团主席、世界著名建筑师张永和进行了专访,就建筑、人文、城市等话题进行了探讨。
在张永和看来,如果一个城市过大,缺乏人的尺度,这个城市和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消极,反过来说,“如果街道的宽度、房子的密度都比较人性化的话,即使这个房子再丑,这个环境可能还是挺宜居的”。

“三联人文城市奖”终审团主席、世界著名建筑师张永和 图片来源:主办方提供
一个建筑最重要的是大小和尺度
NBD:您曾经说过,首先要有好的城市肌理,然后才有人性化的城市。在您看来,建筑如何通过人性化来增进城市的人文属性?
张永和:人,他(她)是一个有限的范围,人走路的每一步,它就这么大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为人设计的生存环境,它应该是有一定尺度的。如果一个城市过大,人一旦不能走的话,这个城市和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消极。
换句话说,一个建筑长什么样子,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它的大小和尺度。
所以可以想象,如果街道的宽度、房子的密度都比较人性化的话,即使这个房子再丑,这个环境可能还是挺宜居的。
NBD:如果说人文城市强调的是人的尺度,是以人的尺度去丈量城市、建筑,那么又该怎么去平衡这种人文属性与经济的效率、秩序和活力之间的关系?
张永和:你提到效率,如果效率意味着速度,那么可能就得质疑“效率”了。因为城市作为几百万、甚至上千万人共同生活的环境,不能只考虑建设的效率,而应该关注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,是不是可持续,人生活在里面是不是能有质量,所以我觉得人文不见得一定跟效率有冲突,但如果有的话,就一定要想清楚什么是优先的。
NBD: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%,再向前发展,可能除了增量建筑那一部分,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存量改造。在这种城市更新和改造过程中,您觉得又该如何去体现人文价值呢?
张永和:新城和旧城,我觉得涉及新旧关系的两个方面:第一,城市里肯定会有更新迭代,不可能每个城市都保护下来变成博物馆,因此新旧的关系怎么搭配就变得格外重要。
我觉得“新”应该是真正带着对“旧”的尊重去做,因为它是一个时间上的延续性,等于是在时间的长河上不断累加,而不是想象历史是被切断的。
新建筑可能携带的基因,它不应该仅仅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特点,而应该是一些更重要的跟人的生活相关的基因。之前我提到建筑的尺度、空间的尺度,这些方面就很重要。
比如窄小的街道,你可以看到马路对面,碰上一个朋友,你过去打个招呼,也许俩人就一块吃个中饭,如果那样的生活是我们想象中比较好的,那么现在的城市动不动好几十、上百米宽的马路就做不到这一点。
“让戏剧更多地发生在社区中间”
NBD:作为普利兹克奖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评委,您如何看待最近两年普利兹克奖得奖建筑,似乎有一些越来越关注社会民生领域的转向?
张永和:我不知道你关注普利兹克奖有多久,如果足够久的话,你可以看出来,它的评奖风格其实是很摇摆的——一会儿想说是不是给这个类型的建筑发个奖,一会儿又想说是不是给另外一个类型的建筑发个奖。如果看过去十年的普利兹克奖,你想建立起来一个好建筑的标准,其实是挺困难的。
但这并不是说它的评选没有质量、或者说不一致,相反,过去这两年从我个人来说,反而是我比较认同的。
因为它选出来的建筑师,实际上是考虑对建筑学本身的贡献。建筑学本身有一套自己特定的知识体系、问题范畴和思想方法,它跟做雕塑就很不一样。
所以如果你回看过去这两年的普利兹克奖,实际上它就是比较关注建筑自身的一些问题,当然它并不是不关注社会、环境,但出发点还是在关注建筑本身。
NBD:最后回到人文城市本身,在您看来,建筑如何才能服务我们的社区公共生活?
张永和:建筑不是一个广告画,它首先应当是实用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设计社区中心,把很多不同的社区需要结合在一起,比如图书馆、体育设施等等,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建筑,
就像我们在湖南吉首设计的桥美术馆,当地居民也许不会专门去看一个美术展,因为它不是生活必需的。

桥美术馆 图片来源:湖南日报
但我们想尽量让艺术离居民更近一点,而不仅仅是我们设计的那个房子。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在美术馆的地板——也就是桥的屋顶上留了两个大天窗,即便你不进美术馆,只要从桥上过,抬头就能看见一点点艺术,也许因此你就发生了好奇心,就会去看艺术展,就会变成艺术爱好者。
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件事,而且我希望建筑师们有机会就做更多这样的项目,让戏剧更多地发生在社区中间,而不是设计一个个封闭的剧院,不管里面的戏有多精彩。